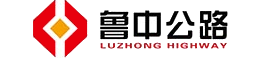姥姥家的山
姥姥家三面都是山。
山连个像样的名字也没有,南边的是南山,北边的叫北山,西边长长的便是长山。
一村的人都指着这一片山。吃的、住的、用的,孩子上学的学费,结婚的新房,都要向山里寻,从山中取。就连人老了,还得从山上找一方好木头打一副寿材,埋入这里,堆成一个个小土包,成了这山的一部分,继续守护着他们的子子孙孙。
每次去姥姥家,只要是不着急赶路,我都会去山上转转,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,召唤着我:来吧!
我去了。
山不高,我却从孩童爬到了中年。后来,我便鼓动着爱人、儿子和女儿一块陪着,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,轻装信步,率性而行。身旁是爱人执手不离左右,儿子则贴身护卫着采花逐蝶、四处乱跑的妹妹,一家四口就这样有一搭,无一搭。肆意地观山峦起伏,赏松柏常青,看狗尾草在风中摇曳,瞧知名不知名的虫儿在草丛间穿梭。兴起时也会大喊一声“你~好~”,声音传出去好远,却从未听到过回响,倒是惊动了在树上休憩的几只斑鸠,扑棱棱逃离到另一座山上去了。偶尔碰到田间劳作的村里人,不免又要有几句寒暄,“忙着了?”“这都多少年不见了?孩子都这么大了!真像你小的时候。”就这样,走走停停,少了攀登之苦,多了闲庭之乐,倒是正好可以趁兴而去,趁兴而归。
山很贫瘠,却像姥姥的笸箩藏满了针头线脑和各种宝贝一样,在漫山遍野的杂草丛、碎石堆里生长着星星点点的庄稼蔬菜,玉米、高粱、地瓜、山豆角、南瓜、冬瓜。地不大,大得像姥姥炕上的凉席,小的像姥姥灶上的锅盖,全凭姥爷一镐一䦆头开出来的。肥是自家沤的农家肥,水是从远处挑来的山泉水,然后一瓢一瓢地浇在苗子的根部。山上缺水,姥爷虽然不知辛劳,但也只能种些耐旱的作物。记忆中每到夏天,姥爷肩头上的箩筐里总少不了新鲜的瓜豆,大锅一熬,便是一大家子的吃食。每当这时候,我总喜欢跟在姥爷屁股后边,只见他有时会拿出一个圆滚滚土豆,有时会是一根裹着绿衣吐着红穗的玉米,扔进烧火的灶里。然后将一些嫩的豆角、辣椒、茄子顺手丢进那缺了口的咸菜缸,缸里红的绿的黄的,颜色便愈发的丰富了。最后,缠着姥姥别忘了灶里的土豆、玉米,那可是最最美味的东西了。
如今姥爷早已不在,开荒的地方也重新长满了荒。风吹过,只有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。看看身边的爱人和一双儿女,环顾这片静卧着的群山,我分明听到熟悉的召唤又一次传来,原来是我那早已远逝的童年。